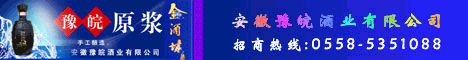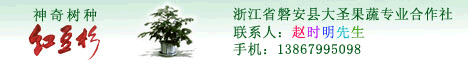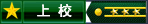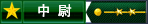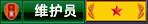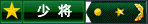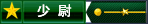二十九
母亲带来的皂角,我们三个人都用,洗过的衣服洁净柔软舒适,还散发出一股清香。
母亲的简短之行,给我们营造了一片心神恬适的荫庇——赔了芦花仔鸡后,社员们一见我们就笑, 处处呵护我们,累活脏活很少让我们干,工分却不少记。这以前,我们总是邋邋遢遢,懒懒散散,吊儿郎当,哪值得同情爱护,是母亲,让这里的一切‘旧貌’换了‘新颜’。
年底,夏进报名参军,凭着他身强体健,苗正根红,体检政审,一帆风顺,穿上了令人眼馋的绿军装,被乡亲们戴上大红花,敲锣打鼓送下了山。
西源知青点就剩下我和刘芳了,我有些失落,晚上寂寞时,有夏进聊天,总比没人聊天好,尽管他结结巴巴。找隔壁的刘芳来说话吗?那会不自在,不成体统。
刘芳却很高兴,越来越喜欢唱歌,越来越喜欢往我这边跑。有一次,她嬉皮笑脸对我说∶“哥,电灯泡没有了……”
“什么意思?哪来的电灯泡?从来就没有啊!”
“哥,你真会装!你当真不懂吗?”
“我真不懂,不知道你说的电灯泡什么意思。”
“不跟你说了,走,洗衣服去!”
洗衣服可以,知青在一起互相帮助,名正言顺。在茅草屋里,一男一女,白天可以冠冕堂皇在一起,做饭看书谈话,晚上不行,没有灯亮,黑灯瞎火在一起,让贫下中农看见,闹出闲话,反映上去,对我对刘芳招工招生都不利,按乡亲们说法,不晓得是驴子不走,还是磨不转。
在我眼里,刘芳还是个小妹妹,豆蔻年华,天真烂漫,不懂世事,一副小鸟依人毫无忌讳的模样。我满十八了,成年人,时时处处要注意,不能落下话柄,传到母亲那里,说我脑子里有邪念,心里头不清净,欺负邻家妹妹。
晨曦中,晚霞里,我们俩一前一后,到村后的水溪边洗漱,洗衣服,几乎天天如此。一到断黑,就各自回屋,闷头睡觉。尽管刘芳一开始还敲土砖墙,我一直不理睬,她就‘偃旗息鼓’了。
后来,朱队长给弄了一盏菜籽油灯,我们才偶然在一起看看书,拉拉呱,但,一到午夜,我就催刘芳回去,说∶“小丫头,回去吧,明天还要出工呢!”
“谁是小丫头!?我十七了,与李铁梅一样大了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!听我姑妈说,你妈妈也是十七岁嫁给你爸爸的!”
“哦,刘嫲嫲怎么跟你说这些?那你的意思是,穷人的孩子早当‘嫁’啰!”我故意逗她。
“谁跟你开玩笑!在这天高皇帝远的遥天辟地,我们俩应该早作打算……”刘芳很认真。
“回去吧,躺床上打算去,看明天是下田插秧还是上山采茶?看样子,我们俩是拴在一起的蚂蚱,都蹦哒不动啦!”
她这才抿嘴笑,临走, 还是恋恋不舍,眼睛里充满幽怨和嗔怪。
许多年后,想起那些事,觉得很奇怪,刘芳的一片真情,我怎么就无动于衷呢?可能女孩子先天发育早,对男女私情,特别敏感细腻丰富。而我,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,一是因为邻家妹妹,不能欺负,二是营养不良,发育迟缓。难道,那就是懵懵懂懂的初恋?
一天晚上,刘芳带过来一本手抄本书——‘少年维特的烦恼’,“看看吧!我不是‘绿蒂’,但愿你也不要做‘维特’……”她眨着眼睛说。
“什么’绿蒂’‘维特’?你哪来的这种书?!”
“你别管!哥,好好看看,你该启蒙了!”刘芳诡秘地笑着。
那天晚上,她没有逗留,我一个人,一口气把那手抄本看完,直到鸡叫头遍……

 Post By:2017/6/5 15:19:28
Post By:2017/6/5 15:19:28




 Post By:2017/6/5 15:20:17
Post By:2017/6/5 15:20:17




 Post By:2017/6/5 16:26:39
Post By:2017/6/5 16:26:39




 Post By:2017/6/6 12:20:49
Post By:2017/6/6 12:20:49


 Post By:2017/6/7 11:25:35
Post By:2017/6/7 11:25:35




 Post By:2017/6/8 8:45:39
Post By:2017/6/8 8:45:39




 Post By:2017/6/8 10:10:37
Post By:2017/6/8 10:10:37




 Post By:2017/6/8 10:29:35
Post By:2017/6/8 10:29:35


 Post By:2017/6/9 10:00:58
Post By:2017/6/9 10:00:58


 Post By:2017/6/9 10:42:05
Post By:2017/6/9 10:42:0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