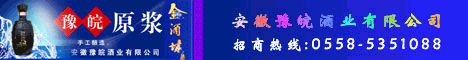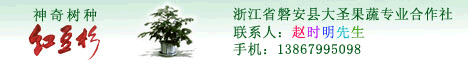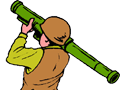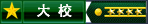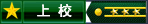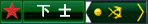|
“别瞎说,干吗开小差。”乔震山笑着说,“紧跟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嘛,谁不举双手赞成,可有的人就不咋的。”说着,笑眯眯地瞟了温明顺一眼。
温明顺听得入迷,忽然被乔震山最后这句话所触动,刷的一下,脸红了。
“你是哪部分的?”刘吉瑞见他面色忧闷,随口问道。
“暂时没有部分。”温明顺把脸一沉,咕噜了一声。
“这是什么话?”刘吉瑞觉得奇怪了,“闹了半天连个部分都没有哇!那你这身军装哪来的,偷的?”
全车人哄然大笑,也随着开起玩笑来:
“准是个混子,要不也是个开小差的。”
“也许有点精神病,找卫生员治一治吧!”
“掉队的吧?难怪情绪不高。”
温明顺可认起真来,他怒不可遏,板着脸,赌气似的一声不吭。他回想起这几天的经历,心里充满了烦恼。
他在锦州战役中受了伤,出院后,部队刚好在前一天晚上从这里出发了。他怎么也打听不着自己部队在哪里,有的说往东开拔了,有的说进关了,谁知道往哪里走了?这时,迎面开来一辆汽车,他伸手挡住了,问道:“同志,你是哪部分的?”司机同志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来:“军部的,上来吧同志,咱们进关了。”他没问三七二十一就爬了上去。“好啦,我们军部的汽车,到军部再说吧。”心里一痛快就睡着了。醒来和司机一谈,才察觉这不是自己军的车子,要下车吧,已经走了这么远,下去怎办?不下车吧,没有介绍信到别的单位,人家不要又怎么办?他哑巴吃黄连心里苦。
温明顺把全部心事告诉了大家,长叹一声,又把头低下。
“喂,别难过,伙计!”乔震山笑眯眯地碰了他一下,“没地方去跟我走,到我们连里,大伙准欢迎你。”
“对,”刘吉瑞接上说,“咱们那连,不是对你吹牛,谁不知道英雄第四连!”
温明顺仔细看了看连长乔震山,他的脸是那么纯朴憨厚,两道黑眉毛底下的大眼睛严肃而又闪露着智慧。温明顺转悲为喜,“行,就跟你们走吧。反正都是自己的军队,在哪里也是干革命。”
刘吉瑞高兴了,凑到温明顺跟前,拍着他的肩膀:“小伙子,到了目的地,你就到我们那个班好啦。我这班长当不好你尽管批评,没问题。以后到连部,请连里写封信给你们单位,把情况说明就得啦。”
两天以后,汽车沿着弯曲的公路奔驰在高山峻岭上,机器吃力地吼叫着,转眼间汽车在两山之间的一个豁口上停下来。乔震山转头一看,两侧的山上,屹立着古老的城堡。大家跳下车,直向山上奔去。他们站在长城上,手扶着城垛口,眺望着这两千年前祖先们建成的奇迹——万里长城。举目所及之处,黑黝黝的长城起伏在群山之上,耸立于云霄之间,连绵不断,消失在天陲线上。
乔震山在抗战时期,曾随部队在长城内外和敌人周旋。长城,在他的眼里也不算陌生了。一瞥之后,他向大家说:“同志们走吧,赶路要紧,不然人家打北平,我们就赶不上了。”
大家正要下山,忽然一个战士喊道:
“嘿!谁在这里写的标语哎!”
大伙扭头一看,果然发现城墙上用石灰水写了几行字。
“这哪里是标语,净瞎张罗!”几个战士同声说。
刘吉瑞看了半天也不明白,反正不是标语。他着急地说:
“走吧,不懂看它干啥!”
“哎,别忙,这字像是我们团长写的。”乔震山站在一块卧虎石上,不眨眼地瞧着。
“对,”刘吉瑞说,“团长当年是北平的大学生,他写的准有道道。连长,你念来听听!”
“念是可以,就是讲不大透。”乔震山微微一笑,清了清喉咙,慢慢地念起来:
巍峨燕山岭,
岭岭舞长城;
叠嶂插青天,
蜿蜒西南行。
南瞰平津原千里,
北眺冀察山万丛。
山万丛,起劲风,
扫尽千年坐地虎,
斩绝万代恶苍龙。
念完,战士们不讲自明,纷纷嚷道:
“嗬,这诗到底比标语味道厚实。”
“咱们团长还真有两下子哩!”
汽车又轰叫起来,向山下开进了。当乔震山他们到达师部驻村时,暮色已笼罩着大地了。
师部在这个村里刚设营完毕,空场上停着不少的马车。饲养员在忙着铡草喂牲口。
乔震山在师司令部报到时,给指导员郝平打了个电话,郝平告诉他:连部和团部都住在靠山镇。
“靠山镇?”乔震山心里一怔,“真巧,住在我的老家!”
二
乔震山带着刘吉瑞、温明顺离开了师部,刚巧碰上团后勤的运输马车,便一起搭车向靠山镇奔去。
几年来的战争生活,乔震山从没认真地想过家。现在,前面的宿营地就是靠山镇了,亲人的影像不由得浮现在眼前。他捏着指头暗暗地给父亲计算着岁数,“嗯!已经六十岁了。”他想到妈,又想到弟弟。弟弟多么可爱啊!圆圆的脸,黑黑的皮肤,两道黑眉底下闪着一双大眼睛,他天真纯朴、聪明伶俐……乔震山的脸上现出了平静的笑容,眉间那两道皱褶舒展开了。
“还有姐姐,”他继续想着,“唉!她现在死了还是活着?要是现在还活着,该……”他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心里充满了愤怒和痛苦。他这突如其来的长叹,引起了身边战士们的惊异。
“连长,伤口痛吗?”刘吉瑞关怀地瞧着乔震山,“到了连部叫卫生员换换药,找个热炕头一睡,准能好。”
是的,他身上曾受过无数次的伤,旧疤新创,每逢阴晴无常的节气,常常隐隐发痛。
“唔……”乔震山漫不经心地答应着。他环视着原野,故土的香气,使他忆起更远的往事……
乔震山原名孙大宝,一九四二年参军后当过侦察员,为了工作的便利才改名乔震山。他的老家是山东惠民县,有父亲、母亲、姐姐和弟弟。父亲是个庄稼人,靠当长工养活孩子老婆,日子过得挺累。大宝十五岁那年,倾盆大雨一直下了五天五夜,黄河决口了,大水像猛兽一样淹没了村庄和田野。大宝一家五口借着一张破床的浮力才逃了出来。逃出来又怎样?倾家荡产了!连个破瓦盆都没带出来。吃什么?穿什么?父亲仰面长叹,母亲垂头落泪,弟弟二宝哭着要吃的。大宝心里很难过,对父亲说:
“爹,不是二叔在天津吗,不好去找他?”
一句话提醒了父亲,于是一家五口向天津出发了。
秋天,大宝一家要着饭来到天津市,按过去写信的地址找了多少地方也没找到。后来听人说,二叔去年因为生活过不下去,和一帮人到蓟县靠山镇扛长活去了。这一下把大宝爹难透了。去还是不去?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大宝说:“去!爹,咱一家五口在这里非饿死不可。”爹同意了。
路上,小弟弟实在可怜,扯着母亲的袄襟嚷脚痛。痛也要走呀!大宝把弟弟背在身上走着,哄着。
秋去冬来,西北风越过长城,飘来了冰冷的雪花。
他们总算来到了蓟县的靠山镇,在街东头三间小草房里找到了二叔,但是,他躺在没有席子的土炕上,身上盖着一块破麻袋,已经瘦得不像人样了。
“老二!”大宝爹轻轻地叫了一声,“你还认得我吧?我是你哥!”
二叔微微转头,有气无力地颤动着嘴唇:
“哥……我……不行了……财主逼租,打……打了我,好……你来吧,种地,还……还他租子。”
全家人,便在二叔的小草屋里住下。不几天二叔就死了,全家人一片哭声。就在这时,一个瘦长个儿走进屋来。这人二十多岁,留着分头,瞪着一对猴子眼,身穿黑大袍,哈着腰,袖口挽起一块,露着雪白的一截,手里拿着鞭子。
“哭什么!”他尖着嗓子大咧咧地叫了一声,然后,看看炕上的死人,又看看他们穿的破衣烂衫,“你们是干吗的?”
大宝扭头说了一声:“从山东逃荒来的,这是俺二叔。”
“那好,”那人凶声凶气地说,“十八斗租子,他死了你们还吧!”
“啊?怪事儿!”大宝爹大吃一惊,“这……这关我们啥事啊?”
“弟欠兄还,理所当然,有什么奇怪的!没有租子有钱也行。”
“逼死人,要偿命,要什么钱!”大宝气冲冲地瞧着来人,小拳头捏得绷紧,看样子要打架。
“嗬!小猴崽子,胆子可不小,敢顶冲老子!”来人骂了一声,扬鞭就打。
“住手,你敢打人!”大宝一伸手把鞭子夺了过来,往地上一丢,“告诉你,我们人穷骨头可不穷。”
“对,逼死人要偿命!”大宝爹把袖子一挽,“走,上街说理去。”
那人转动着一对猴子眼,环视着屋里的人们,最后,目光在大宝的姐姐桢英身上停下了,这山东姑娘,虽然穿得破烂,但她那俊秀的脸蛋,匀称的身材,在靠山镇来说,要算是顶天的美人了,若把她献给五爷,准能捞一笔不小的款子。这使他满脸的怒火霎时烟消云散,立即变成嬉皮笑脸了。
“咦!你这姑娘……”他伸手去摸她的下巴颏。
大宝眼疾手快,啪的一声把那人的手打开了。那人吃惊地摸着被打红的手背,倒退了一步,改口说道:
“算了,算了!人死了嘛,埋了就算了。至于租子,不要紧,还不起以后再说。你们既然千里迢迢地来了,那就在这里住下吧,有房子住,也有地种,这都是我们五爷给佃户的。噢,你们大概还不认识我吧,我叫鲁青,大家都叫我二东家。其实我哪里是东家,不过是遵五爷的嘱托,在这里看看房产、收收租子而已。佃户们哪个不说我是个好人。”鲁青说话时,不断地转动着两只贼溜溜的眼,瞟向大宝的姐姐。这时的鲁青和才进来时完全变成了两个人,是那样的和气、殷勤。临走时还答应送他们一斗粮食过冬。下午,果然照办了。
大宝爹有心不收吧,隆冬数九,远道他乡,粮无一粒,钱无分文,一家五口可怎么过呢?万般无奈,只好收下了。
大宝虽然才十五岁,却看出鲁青的诡计贼心,他说:
“爹,这粮食咱不能要。我看这人鬼头鬼脑,准没安好心。”
大宝爹点点头,长叹一声:“先这么办吧,孩子,总得活下去啊!”
就这样,他们一家算是在靠山镇落户了。
不料生活折磨,远途操劳,大宝爹又得了重病,全家的生计,全部落在这少年身上。一家五口靠一斗粮过冬,怎能过得去呢?明年的种子由何而来?左算右算还是过不去。于是大宝冒着严寒,穿着单衣,进山打柴,朝出晚归,有时深夜不回,全家的吃食,就靠他的一柄斧子、一条扁担来负担。
| 
 Post By:2021/8/7 19:11:29
Post By:2021/8/7 19:11:29


 Post By:2021/8/8 9:34:56
Post By:2021/8/8 9:34:56


 Post By:2021/8/14 12:13:52
Post By:2021/8/14 12:13:52


 Post By:2021/8/27 16:08:20
Post By:2021/8/27 16:08:20


 Post By:2021/8/27 16:08:51
Post By:2021/8/27 16:08:51


 Post By:2021/8/27 16:10:13
Post By:2021/8/27 16:10:13


 Post By:2021/8/27 16:11:07
Post By:2021/8/27 16:11:07